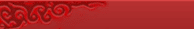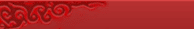|
上文提到的土地资源配置准则,不是小事情。背景已设定:香港政府独家向市场供地,大陆这里则是多级、多个政府竞相向市场供地。“政府之间的竞争”又很特别:甲政府卖出一块高价地,乙政府欲与之“竞争”,只能在自己的行政范围内多供一块地,争取把甲地的需求“拉”到乙地来。
本来“高价土地”反映出的信息,是那个位置很不错。一般而言,紧靠好位置的土地,其位置也不错。所以市场里一旦冒出来一块高价地,通常总会刺激四周的地价上升,直到高地价带来的净收益递减,地价才沿着离开中心的距离而递减。
不妨看一个集市吧。最早也许有人发现在某个位置摆摊比较“招客”,生意好做;其他商贩凑热闹,到那个位置竞相摆摊,自发成就了一个集市。在理解上,卖家与卖家凑到一起,争的是买家“客似云来”;买家与买家挤到一起凑热闹,图的则是“货比三家”的便利。大家熙熙攘攘地争来斗去,“人气”聚,生意旺,摊位租上升,地价也就上升了。
这样自发形成的市场,自发形成的中心,总有一股自发的吸引力,把周遭的商贩、顾客以及为商户、顾客服务的生意,不断“拉”入市场,聚成更畅旺的市场和更有人气的集聚地。市镇就是这样起来的,城市和形形色色的“中心”,一般来说也是这样起来的。
商贩和顾客凑到一起的种种好处,要被“成本”抵消。传统时代,人们主要靠步行,“赶集”就不可能走得太远。施坚雅(G.W.Skinner)发现在川西传统农村,任何一个村子向不同的方向走上个把小时,总有一个集市存在。这说明集市网络的覆盖密度,受到步行距离的制约。既然那时的农民走不太远,所以集市的规模也不可能太大。不像现在火车、高速公路和飞机都通达的大都市,聚几千万人都不在话下。
这件事情上,普通人面临的选择,无非是花多大代价才能享受“集聚点”的好处。在走不能走太远的传统时代,老乡们平常住在离农地不远的村庄里,隔三差五赶赶集,有点交易和社交活动也就不错了。工业化以来,人口与经济集聚的净收益增加了,农民进城和大规模城市化才逐渐成为普遍的选项。至于在大都市里当宅男宅女,那只有“后现代社会”才可想象。
无论哪个时代,选位置的经济准则总有相通之处:人口与经济集聚的中心处地价最高,然后向外递降;在一个合适距离之外,又鼓起一个集聚的中心,也是中心地价高、四周低;在一个较大的空间里,一个个集聚的中心可以用一个个地价等高线描述的圈圈来表达。这背后的行为基础蛮可靠的,这就是人们总是按追逐较高净收益的经济准则,择地而居。
从这点看,政府与个人、公司也没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同。当然,政府追逐的“净收益”,比个人、公司有更多社会方面的内容,包括诸如合法性、公众拥护、民意等等,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问题是,政府作为一种行政组织,受到一些很特别的约束,势必限制政府追逐较高净收益时的选择空间。
比较显著的,是政府的行政权力受到行政区化的范围限制。说得直白一点,政府只能“画地为牢”。上文讲过的,村里的农民可以出村赶集,只要跑得动,可以到邻村、邻镇的市场去摆摊、去购物。政府就不行了。作为一个行政组织,它只能在自己的行政区划内行使权力。以土地利用为例,乙地政府有权做的,只是出让乙地之土地,而断然无权出让甲地的土地。在这样一道硬约束下,对任何非本地范围内的市场机会——如集聚带来更有价值的“位置资产”——本地政府既不能扑过去投资,也不能增加外地高地价区的土地供应。它惟一可以做出的反应,是增加本地的土地供应,也增加向市场出让土地。
这就好比乙村农民要去甲镇赶集,但乙村政府说,肥水不落外人田,咱们这里也供块地办个市场不就结了!村民问,咱自己咋就能办个市场哩?乙村长答:咱村办集市的地价比甲镇便宜。这里提出一个经济问题:当甲镇的集市产生集聚效果时,进一步扩大集市面临哪些选择?具体讲,究竟在甲镇多供一块地来扩大集市,还是在乙村——或在丙村、丁村等等——多拿出一块地来新办集市?答案是比较净收益。如果扩张甲镇集市的净收益高于新办集市的净收益,多供甲镇的土地,让乙、丙、丁村的农民自由到甲镇赶集,最优;反过来,新办市场带来更高净收益,那就多办几个吧。
但前提是存在一个打通了的土地市场,各家算各家的账,以便对市场机会做“理性的”反应。倘若“画地为牢”一下:乙村仅有权出让乙村之地,答案就变了。道理也简单,扩建甲镇集市的土地净收益再高,却只归甲镇而不归乙村,那对于只有权出让乙村之地的乙村政府来说,还不如另起炉灶,在乙村也办他一个新集市最优!
有人说对乙村的农民不也如此吗?倘若土地私有,他们也只能卖乙村自已家的土地。甲镇扩建市场之利,对无权出让甲镇土地的乙村农民来说,难道不也是子乌虚有吗?此问有理。但是乙村农民不但可出让本村土地,还可以去甲镇经商、投资,所以他们还可以做以下权衡:究竟冒很大的风险在本地新建一个人气不足的集市,还是到甲镇分享扩建那里的集聚之利?反正经济史的结果很清楚,任何时代的集市都集聚在某些点位,从来没有村村都设集市这回事。
画地为牢的政府却没辙了。作为本地政府,其行政和经济权力差不多都是属地化的。对它们来讲的最优解,也只能是增加本地范围内的供地,兴建本地范围内的设施和其他项目,才能收取本地范围内的净收益。在本地范围内,如果建市场用地的净收益大过种玉米(2447,-5.00,-0.20%),建市场就是了。至于在本村新建市场还是到邻镇扩大既有市场,究竟何者更优,那个问题就不归本地政府考虑了。
本文涉及一个大话题,就是“地方政府竞争”。近年很流行的一种解释,就是中国高速增长的“密码”,是神奇的地方政府之间竞争。顺便评论一句,“竞争促增长”的理念一般来说对,但阿尔钦早就讲过,处处有竞争,而经济学者的任务是调查实际竞争所受的制约条件,从而理解不同约束下的竞争,有不同的行为逻辑,也有不同的后果。“画地为牢”下的土地资源利用,与统一土地市场下的“自然”状态,有不小的分别。政府争相供地,当然也是一种竞争,但从现象观察和逻辑推演两个层面看,此种竞争并不能提升人口与经济集聚进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更优的办法有没有?有的,那就是让土地与画地为牢的行政权力脱钩,回归普通的、能够对更大范围的市场机会作出反应的财产权利。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