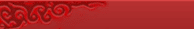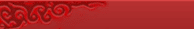|
对于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超预期回落,既不能反应过度,也不能掉以轻心。现在“稳增长”,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不是简单地放松宏观调控政策,不是重返“高增长”,不是再次回归GDP崇拜、GDP追求,而是在新形势下,向各级政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是“稳增长”要与转方式、调结构、控物价、抓改革、惠民生相结合,努力实现科学发展。
一、当前中国经济走势:超预期较低位运行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出现了比社会预期更为明显的放缓。从GDP季度同比增长率来看,今年第一季度承接了去年4个季度连续回落的态势(去年4个季度分别为9.7%、9.5%、9.1%、8.9%),进一步回落到8.1%,低于社会上的普遍预期 (普遍预期为8.4%或8.5%)。这是自2009年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回升以来,12个季度中的最小增幅;也是自2000年起,12年来少有的6个低于8.1%的季度增长率之一 (另外5个低于8.1%的季度增长率是:2000年第四季度,7.3%;2001年第二季度,7.7%;2001年第三季度,7.8%;2008年第四季度,7.4%;2009年第一季度,6.6%)。
从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同比增长率来看,今年也承接了去年7月以来的回落态势,4月份进一步下降到9.3%,亦低于社会上的普遍预期(普遍预期为12.2%)。这是自2009年6月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回升以来,35个月中的最低增幅;也是自2000年1月—2月以来,148个月中少有的14个低于10%的月同比增长率之一(其他13个低于10%的月份是:2001年7月、9月至12月,2008年10月至2009年5月)。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同比增长率9.6%,虽比4月份略高0.3个百分点,但仍处于10%以下的较低位运行。
对于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超预期回落,既不能反应过度,也不能掉以轻心。“反应过度”的主要表现为:一是主张大力度地放松宏观调控政策,二是刚刚沉寂一点的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危机论、中国经济硬着陆论、中国经济滞胀论等说法又浮出水面。“不能掉以轻心”就是要认真分析经济增速明显回落的各种可能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措施,避免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保持经济更长时间的平稳较快发展。
二、原因分析: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经济增速的进一步回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从学术界已有的分析看,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主动宏观调控的结果。
其二,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调整的结果。
其三,国际上外需低迷、出口不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发酵。
其四,国内消费动力不足、投资需求不旺。
其五,资源、环境、劳动力供给等约束强化,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
其六,企业经营困难,各种成本上升,资金紧张,市场需求疲软,利润下降。
其七,经济增速回落过程中有惯性。
以上的原因都存在。这里,我们想强调提出的是,可能还有第八个方面的原因,即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一些地方在反对GDP崇拜、反对盲目追求和攀比GDP的过程中,出现了忽视GDP、淡化GDP的倾向,不再下大力去做好经济工作。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
从历史上看,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情况表明,每个五年计划(或规划)之后的第二年,又是各级领导班子换届之年(我们称之为“双重推动年”),往往容易出现经济增长趋热的态势。改革开放以来,从“六五”计划到“十一五”规划,共有六个这样的“双重推动年”,即1982年、1987年、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其中,有三个年份是经济增长较热或过热之年 (1987年11.6%、1992年14.2%、2007年14.2%),有两个年份是经济增长回升年 (1982年由上年5.2%回升到9.1%、2002年由上年8.3%回升到9.1%),仅有一个年份是经济增长回落年(1997年由上年10%回落到9.3%)。今年又是这种“双重推动年”,按照历史惯例,本应着重防止经济增长趋热,但实际情况却相反,出现了经济增幅的较大回落。当然,这也可能像1997年那样,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影响。但如果存在上述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则是需要重视的。
为什么不可忽视GDP?GDP(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常住单位参与生产和服务活动所形成的增加值。物质资料生产,以及相关的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活动,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稳定发展的实体经济基础。当然,在现实经济运行中,GDP增长速度不能太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曾多次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大起大落”的要害就是“大起”。因为经济增长速度过高、过急、过快的“大起”,也会很快产生“四高”问题,即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通胀,很快造成对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各种均衡关系的破坏,由此而导致随后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大落”。因此,反对GDP崇拜、反对盲目追求和攀比GDP,是正确的。但我们也应知道,在一定时期内,GDP增长速度也不能太低。如果太低,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一者,会给居民收入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困难。因为GDP是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GDP“蛋糕”做大了,不一定就能分好;但如果没有GDP“蛋糕”的适度做大,也就更难去分好“蛋糕”。二者,会使财政收入受到影响。财政收入若大幅下降,则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实现,都会受到影响。三者,影响企业的宏观经营环境。较低的GDP增长,从需求面反映市场需求疲软,影响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影响就业的扩大。总的来看,经济增速过高,会恶化经济结构;而增速太低,也会恶化经济结构。经济增速过高,难以持续;而增速太低,也难以持续。因此,要保持一定的、适度的经济增速。
现在“稳增长”,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不是简单地放松宏观调控政策,不是重返“高增长”,不是再次回归GDP崇拜、GDP追求,而是在新形势下,向各级政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是“稳增长”要与转方式、调结构、控物价、抓改革、惠民生相结合,努力实现科学发展。
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多高、多低为宜?这涉及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把握问题。
三、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应保持一个渐进过程
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近两位数增长,现在进入到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但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
首先,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是一个突变过程,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有学者提出,2013年—2017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由10%的高速降到6%—7%的中速,明显下了一个大台阶。然而,我们从国际经验看,不同国家因其地域大小不同、人口多少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国内外环境条件不同等,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表现为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有的国家表现为突变过程。如日本,二战后经历了4个阶段:
(1)1953年—1959年的7年中(1952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7.2%。
(2)1960年—1973年的14年中(1959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上升到9.7%。
(3)1974年—1991年的18年中(1973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明显下降到4.1%。
(4)1992年—2011年的20年中(1991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又显著下降到0.7%。
第二种情况,有的国家则表现为相对平稳的渐进过程。如韩国,二战后也经历了4个阶段 :
(1)1954年—1962年的9年中(1953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3.9%。
(2)1963年—1979年的17年中(1962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上升到9.5%,其中有5年GDP增长率的峰值为11%—14%。
(3)1980年—1997年的18年中(1979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略下降到8.2%,仅下降了1.3个百分点,其中有4年GDP增长率的峰值为11%—12%。
(4)1998年—2011年的14年中(1997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明显下降到4.2%。
第三种情况,有的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后,在一定时期随着科技发展等因素的推动,还可能重新上移。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在以IT产业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潜在经济增长率又有所上升。二战后,美国亦经历了4个阶段:
(1)1953年—1973年的21年中(1952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3.45%。
(2)1974年—1992年的19年中(1973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下降到2.65%。
(3)1993年—2000年的8年中(1992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又上升到3.5%。
(4)2001年—2011年的11年中(2000年为基年),GDP年均增长又下降到1.57%。
每个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究竟是多少?难以给出精确测算。在宏观调控实践中,这也是一个经验把握问题。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过程中,如果现实经济增长率过快、过急地下落,有可能引起经济和社会震荡。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社会各方面(政府、企业、个人)都要有一个适应过程。为了避免带来经济和社会震荡,宏观调控应力求使经济增长率下移成为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由高速(10%)先降到中高速(8%以上、10%以下),再降到中速 (7%—9%),再降到中低速(6%—8%)和低速(5%以下)等等,分阶段地进行。当然,现实经济生活不会完全按照人们的主观意志运行,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把握经济增长率的平缓下落。特别是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国内需求的回旋余地较大,工业化、城镇化的纵深发展都有一个逐步推移的过程,可以说,有条件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平滑化。
其次,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对其上下限下移的把握可以不对称。
我们曾根据我国1978年—2009年GDP增长指数,利用HP趋势滤波法,得到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计算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中,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大体处于8%—12%区间,即上限为12%,下限为8%。现在,当我们考虑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情况时,并非上限、下限都要同时下移。在最近一段期间,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把握中,可以首先将其上限下移2个百分点,即降为10%以内,而下限8%则可暂时不动。这是因为过去我们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往往容易冲出10%。实践表明,经济增长率冲出10%,就会使经济运行出现偏快或过热的状况而难以为继。现在,从资源、能源、环境等约束不断强化的情况出发,我们首先应该把经济增长率的上限降下来,把握在10%以内比较妥当。
多年来的实践还表明,经济增长率8%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基本底线。若低于8%,如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下降到7.6%和6.6%,给企业生产和城乡就业带来严重困难,使全国财政收入呈现负增长。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降到8.1%,各方面也立即感到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使企业经营和国家财政收入再度紧张。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长预期目标由原来多年的8%降为7.5%,主要是导向性的,引导各方面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但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把握中,仍以8%作为适度增长区间的下限为宜。
由此,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操作中,当经济增长率冲出10%时,就要实行适度的紧缩性政策;当经济增长率低于8%时,就要实行适度的宽松性政策;当经济增长率处于9%左右的区间时,经济运行状况比较良好,可实行中性政策。如果说我们过去在宏观调控中经常要把握好经济增长率的 “峰位”,防止“大起”,那么今后,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则要特别关注经济增长率的“谷位”,防止“大落”。
最后,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并非经济增速一年比一年低。
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就年度经济增长率来说,并不一定是直线下落的,也就是说并不一定是一年比一年低,年度间仍会有高低波动。比如,国内外许多经济预测机构都预测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比2011年低,但在预测2013年时,一般都认为会比2012年略高。
为什么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比2012年略高?我们简要回顾一下2008年应对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来,我国宏观调控侧重点由“保增长”到“稳物价”,再到近期转为 “稳增长”的过程。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的两年半期间,为了迅速扭转经济增速明显下滑趋势和促进经济企稳回升,宏观调控的侧重点是“保增长”。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了“一揽子”刺激计划,到2009年第二季度之后,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急速下滑的态势,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总体回升向好,走出一个“V”形回升轨迹。2009年经济增长率为9.2%,仅比上年回落0.4个百分点。2010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10.4%。随着经济回升和货币信贷超常增长,从2010年1月起,物价开始新一轮逐月攀升,连续破三、破四、破五,到2010年11月居民消费价格月同比上涨率攀升至5.1%。
在此背景下,201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强调“坚决防止借‘十二五’时期开局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强调 “把好流动性这个总闸门”。这样,在“稳物价”的努力下,2011年7月物价涨幅攀升到6.5%的峰值后,又逐月回落下来,到2011年12月回落至4.1%。与物价涨幅的回落相伴随,2011年经济增长率回落至9.2%,比上年低1.2个百分点。进入2012年,物价涨幅继续回落,5月份回落至3%,这就为防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宏观调控实施适度宽松的微调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到2012年5月,当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以及进出口增长等经济指标出现明显下降之时,又提出宏观调控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由此,一系列相关措施出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鼓励投资,推进“十二五”规划项目的实施,结构性减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等。与2008年至2010年的“一揽子”刺激计划相比,这次的刺激力度不需要那么大。这样,如果国内外经济环境没有重大的意外冲击,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速有望进入小幅回升通道,明年经济增速有望略高于今年。
从年度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看,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第11轮周期)。到今年年底,本轮周期已进行3年。2010年、2011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4%和9.2%,2012年预计为8.5%。本轮周期不会像第9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2+7”周期,即2年上升期加7年平稳回落期;也不会像第10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8+2”周期,即8年平稳上升期加2年回落期。本轮周期有可能走出一个新的轨迹,即锯齿形的缓升缓降轨迹。
四、内需动力:重消费,但不可忽视投资
与前述忽视GDP倾向相伴随的,还有忽视固定资产投资的倾向。
有学者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种增长的动力结构不可持续,必须改变。这里,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说近十余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种增长的动力结构需要改变,这是正确的。因为统计数据表明,近十余年来(除2005年),我国投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连续大于消费需求的贡献率和拉动。但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则不符合实际情况。从我国消费、投资、净出口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的统计数据看,1979年—2001年的前23年间,除1993年、1994年、1995年的3年外,其他20年均是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大于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只是从2002年起至2011年的近余十年间(除2005年),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才大于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同时,数据表明,1979年—2011年的33年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5%的只有10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超过2个百分点的只有7年。从支出法GDP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并不起主导作用。
近十余年来,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连续大于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主要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结果。在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既会带动消费上升,也会带动投资上升,但相比之下,对投资的带动更大,这也反映在支出法GDP总量中,投资所占的比重即投资率不断上升,而消费所占的比重即消费率连续下降。图中绘出了我国1952年—2010年消费率、投资率和城镇化率3条曲线。从图中看到,消费率从2001年—2010年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投资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消费率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1年的48.2%,下降了14.1个百分点。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11年的49.2%,上升了13.9个百分点,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率首次超过消费率。
从图中我们还看到,2001年—2011年,城镇化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与投资率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关系。1952年—2011年,从投资率与城镇化率的相关关系来考察,可以分为七个阶段(见图):
(1)1952年—1960年的9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城镇化初期阶段,投资率上升,城镇化率亦上升。城镇化率由1951年的11.8%,上升到1960年的19.7%,年均上升0.88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同向上升中的强正相关,相关系数高达94%。
(2)1961年—1964年的4年,处于“大跃进”之后的经济调整期,投资率下降,城镇化率亦下降。城镇化率由1960年的19.7%,下降到1964年的18.4%,年均下降0.33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同向下降中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51%。
(3)1965年—1977年的13年,这是处于“文化大革命”特殊时期,投资率上升,但城镇化率下降 (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镇化率由1964年的18.4%,下降到1977年的17.6%,年均下降0.06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一上一下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56%。
(4)1978年—1982年的5年,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的调整期,投资率下降,而城镇化率上升。城镇化率由1977年的17.6%,上升到1982年的21.1%,年均上升0.71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一下一上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98%。
(5)1983年—1993年的11年,投资率上升,城镇化率亦上升,与上述第(1)个阶段相同。城镇化率由1982年的21.1%,上升到1993年的28%,年均上升0.62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同向上升中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55%。
(6)1994年—2000年的7年,这是一个应对1992年—1993年经济过热和随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时期,与上述第(4)个阶段相同,投资率下降,而城镇化率上升。城镇化率由1993年的28%,上升到2000年的36.2%,年均上升1.1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一下一上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96%。
(7)2001年—2011年的11年,这是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投资率明显上升,城镇化率亦明显上升。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6.2%,上升到2011年的51.3%,年均上升1.37个百分点,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化率上升最快的时期。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像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样表现为强正相关,相关系数高达94%。
可见,近十余年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连续大于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主要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结果,有其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是不可持续的。然而,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还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城镇化过程。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今后一段时期内,城镇化率的提高不一定有前十年那么快,但是还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期。城镇化的发展,特别是城镇化质量的进一步提高,都还需要适度的投资。同时,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不是说说而已,也需要一定的投资。比如:发展现代农业;加强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保障房等民生工程建设,都需要一定的投资。要重在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扩大投资资金来源,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向我们的经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之,在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中,我们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据此,我们要重消费,但也不可忽视投资。一定的、适度的投资,仍然是一定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