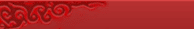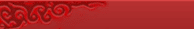|
摘 要 城市转型是指城市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发生重大的变化和转折,它是一种多领域、多方面、多层次、多视角的综合转型。过去,中国城市大多走的是一条以高增长、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型发展道路。在这种粗放型发展模式下,中国城市发展出现了无序和低效开发、城乡区域发展失调、社会发展失衡等诸多弊端,显然这是不可持续的。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正处于加速转型和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必须尽快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面转型,建立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和谐有序的新型科学发展模式,走集约、创新、融合、和谐、绿色、特色发展之路。
关键词 城市发展;城市转型;发展模式;全面转型战略
1 引言
城市转型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它是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演化的。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看,城市发展的历史就是城市转型的历史(侯百镇,2005)。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资源和环境压力的日益加大,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城市转型的热潮。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对现行的城市发展模式进行反思,有关城市转型的多学科、多视角、多维度的综合研究日益增多。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规划学等领域的学者都加入了这一研究行列。有关紧凑城市、精明增长、生态城市、低碳城市、创新城市、创意城市、宜居城市、智慧城市等种种构想,在某种程度上都包含着城市转型的思想。可以认为,城市转型是当前城市科学研究的一个理论前沿课题,也是学界、政府界和新闻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
在国外,转型研究主要集中在原计划经济国家城市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城市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型和资源型城市转型等方面(李彦军,2009a)。在国内,城市转型研究近年来也日益增多,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城市转型的一般性研究,包括城市转型的界定、内涵、模式、动因和方向等(李国平,1996;侯百镇,2005;朱铁臻,2006;李彦军,2009b;孙耀州,2010);二是对城市某特定领域转型的研究,如对城市经济转型(裴长洪、李程骅,2010;李学鑫等,2010)、城市产业转型(潘伟志,2004)、城市发展转型(崔曙平,2008)、城市竞争转型(连玉明,2003)等的研究;三是针对问题城市和典型城市转型的研究。除了大量的有关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研究外,一些学者还探讨了老工业基地以及上海、南京、深圳等典型城市的转型问题(陈建华,2009;吴月静,2009;郑国、秦波,2009);四是从多维度、多视角对城市转型的综合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吴缚龙等人(2006)的研究。近年来,海外有关中国城市转型问题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代表性著作有弗里德曼(Friedmann,2005)的《中国的城市变迁》(China's Urban Transition)和邢幼田(Hsing,2009)的《城市大转型:中国的政治与不动产》(The Great Urban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and Property in China)。
虽然目前有关中国城市转型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但研究基础仍然较为薄弱,尚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概念比较混乱,不同学者对城市转型的界定不一,尚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二是对城市转型的理论基础、动力机制、综合效应和战略路径等方面的认识还较为模糊;三是对单个城市、特定领域转型的研究较多,而从整个国家层面的系统综合性研究较少。本文试图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在对中国现行城市发展模式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当前中国城市转型的内涵、推动因素及其战略思考。
2 现行城市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
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发展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外延扩张的发展道路,属于一种典型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以高增长、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为基本特征。
高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特征。1979~2008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8%,其中2001~2008年达到10.2%。这种高速增长态势主要是依靠城市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来支撑的。以2007年为例,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生产总值汇总的增长率为14.2%,而全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15.3%,其中市辖区增长率高达15.6%[1]。从1978~2009年,中国城市化率由17.92%迅速提高到46.59%,平均每年提高0.92个百分点,其中1996~2009年平均每年提高1.25个百分点。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目前城市经济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力量。2008年,仅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实现生产总值就占全国的62.0%,其中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占全国的64.5%和71.4%。
这种高增长是建立在资源的高消耗和“三废”的高排放之基础上的。2007年,中国GDP约占世界总量的5.9%(UNDP,2009),而水泥消耗占世界的47.3%(2006年数据),一次能源消耗占16.5%,其中煤炭占41.1%,石油占9.2%(BP公司,2009),粗钢表观消费量占32.4%,钢产品表观消费量占33.9%(WSA,2009)。按照国际能源署(IEA,2009)发布的数据,2007年中国CO2排放量已占世界总量的21.0%,尽管中国人均CO2排放量与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只相当于OECD国家的41.8%,但单位GDP CO2排放强度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16倍,是OECD国家的5.37倍。中国经济的这种高消耗、高排放特征在城市得到了集中体现。目前,尽管中国的城市化率还不高,但绝大部分资源都是由城市消耗的。中国经济的高消耗、高排放主要是城市经济的高消耗、高排放,节能降耗减排的关键在城市。以能源消费为例,在2007年中国终端能源消费中,非农产业和城镇生活消费占82.4%;在生活能源消费中,城镇占62.6%;城镇人均生活用能量是农村地区的2.05倍。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08)提供的数据,2005年中国41%的城镇人口却产生了75%的一次能源需求,这与世界发达国家形成鲜明的对照。在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城镇人口的比重一般都高于城市一次能源需求的比重(表1)。这一方面反映了目前中国巨大的城乡差距,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城市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外延扩张特征。
表1 2005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城市能源使用状况(%)
|
城市一次能源
需求比重 |
城市人均一次能源需求相比地区或国家平均水平 |
城市化水平 |
|
美国 |
80 |
0.99 |
81 |
|
欧盟 |
69 |
0.94 |
73 |
|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78 |
0.88 |
88 |
|
中国 |
75 |
1.82 |
41 |
资料来源:IEA,Word Energy Outlook 2008,第182页。
与此相对应的是近年来中国城市的高速空间扩张。自“十五”以来,中国城市建成区和建设用地规模迅速扩张,其增速远快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2001~2008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分别年均增长6.2%和7.4%,而城镇人口年均增长仅有3.55%。特别是,在“十一五”期间,尽管城镇人口增速明显放慢,但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仍保持7.23%的平均增速,远高于城镇人口年均2.57%的增速(表2)。这说明,近年来中国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严重不匹配,土地的城市化远快于人口的城市化。就城市平均规模扩张来讲,从1996~2008年,中国平均每个城市建成区面积由30.4 km2扩大到55.4 km2,平均每个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由28.5 km2扩大到59.8 km2,分别增长了82.2%和109.8%。从某种程度上讲,近年来中国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土地的“平面扩张”来支撑的。
表2 中国城镇人口与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年均增长比较(%)
|
年份 |
城镇人口 |
城市建成区面积 |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
|
2001~2005 |
4.13 |
7.70 |
7.50 |
|
2006~2008 |
2.57 |
3.73 |
7.23 |
|
2001~2008 |
3.55 |
6.20 |
7.40 |
注:2005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缺北京和上海数据,系采用2004和2006年数据的平均值替代。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08)和《中国统计年鉴》(2009)计算。
中国城市的高速空间扩张,也引发了行政区划变化(如撤县(市)设区)以及新区建设和产业园区扩张。近年来,中国一些大城市曾掀起过撤县(市)设区或建设新区的浪潮,规划的软约束和规划界的利益驱动助长了这种大城市空间规模扩张冲动。由于大城市的加快撤县(市)设区,加上国家近年来对新设建制市的冻结,导致近年来中国城市的数量减少,由1997年的668个减少到2008年的655个,减少了13个。其中,“十一五”前三年减少了6个。不少大城市新区的规划面积动辄数百平方公里,有的甚至达上千平方公里,如上海浦东新区为1 210.41 km2,天津滨海新区为2 270 km2,重庆两江新区为1 200 km2。在某些城市,产业园区的规划面积也超过了100 km2。大规模撤市设区和建设新区的热潮,导致全国大城市数量不断增加,中小城市呈萎缩状态。若按城市市辖区总人口计算,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中,2008年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比2005年增加了11座,而中小城市减少了10座[2]。城市用地规模高速扩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城市政府热衷于依靠卖地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从2006~2008年,全国城市土地出让转让收入分别为881.91亿元、1 668.68亿元和2 105.45亿元,占城市维护建设市财政资金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7.6%、38.2%和40.6%,两年内提高了13个百分点。显然,城市的“土地财政”特点推动了城市空间规模的高速扩张趋势。
[1] 计算市辖区增长率时未包括广东省云浮市和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2] 从2005~2008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从286座增加到287座。
3 粗放型城市发展模式的弊端
这种以高增长、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型城市发展模式,带来了城市空间的无序或低效开发、城乡发展失调、社会发展失衡、大城市迅速蔓延等诸多弊端。
3.1加剧了城市空间无序和低效开发
受这种粗放发展模式的影响,目前中国城市空间无序开发现象十分严重,主要体现在:①一些大城市“贪大求全”、“好高骛远”,全国有183个城市提出建国际大都市,40个城市要建CBD,盲目向伦敦、纽约、东京看齐。②前些年各地不管有无条件都竞相建设开发区,开发区数量多、面积大,出现“征而不开”、“开而不发”,造成大量耕地闲置撂荒现象。后来经过长达3年多的清理整顿,到2006年12月,全国各类开发区由6 866个核减至1 568个,规划面积由3.86万km2减少至9 949 km2。③沿海一些城市地区开发强度过高,资源环境压力较大。目前,深圳的开发强度已达到40%,东莞达到38%,远高于香港(19%)、日本三大都市圈(15.6%)、法国巴黎地区(21%)和德国斯图加特(20%)的水平(杨伟民,2008)。某些大城市地区有变成大范围水泥地连成一片的“水泥森林”的危险,其宜居性不断下降。④城市用地结构不合理,工业用地比例偏高,居住和生态用地比重偏低。2008年,全国城市工业用地规模高达8 035.16 km2,占全部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20.5%,而生态用地比重不到10%,居住用地比重只有28.8%。⑤各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多依靠土地的“平面扩张”,土地和空间利用效率较低,尤其是一些城市大建“花园式工厂”,各种形式的“圈地”现象严重。从空间开发角度看,可以认为,过去有些城市的工业化是以牺牲人的福利为代价的,工业用地规模过大、价格偏低、比重过高,利用效率太低。
3.2加剧了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协调
这种不协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地区间城市发展不协调。目前,中国城市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三级阶梯”特征,即东部城市发展水平最高,东北城市次之,而中西部城市较低。如果以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平均水平为100,2007年东部城市人均生产总值相对水平为148,东北城市为96,而中部和西部城市分别只有63和56。同期,西部城市人均工业总产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和支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分别相当于东部城市的24.7%、54.2%、41.1%、23.8%、35.6%和45%。
二是不同规模城市间发展不协调。由于资源垄断和行政配置特点,加上市场趋利原则的导向,各种要素和资源向大城市和行政中心高度集聚,形成典型的极化特征,导致特大、超大和超特大城市过度膨胀,有的已经出现明显的“膨胀病”,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育不足,人均占有资源有限,公共服务能力低,基础设施落后,有的甚至呈现萎缩状态。大城市与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发展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
三是城乡之间发展不协调。中国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且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呈不断扩大的态势。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高达3.33,而1985年该比例只有1.86,1997年只有2.48。更重要的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比2004年扩大了3.7%。
四是人口与产业分布不协调。近年来,各地政府都高度重视积极引导产业向各类园区和城镇地区集中,但对人口集聚和外来农民工安家落户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一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城市群在大规模集聚产业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地大规模集聚人口,由此造成就业岗位、产业分布与人口分布严重不协调,全国上亿的农民工虽然参与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却没有相应地公平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2008年,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集中了全国52%的投资和62%的生产总值,但却只容纳28.3%的人口,人口份额与生产总值份额之比高达1︰2.19;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人口占全国的15.11%,但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32.18%,二者之比高达1︰2.13。相比较而言,在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一些大都市区人口和GDP的份额基本上是相匹配的(李国平、范红忠,2003;蔡翼飞,2010)。 2000年,美国核心发达区域人口份额与GDP份额之比为1︰1.21,日本东京都、大阪府和神奈川县为1︰1.36,英国大伦敦、大曼切斯特和西米特兰为1︰ 1.24(李国平、范红忠,2003)。很明显,人口与产业或经济活动分布严重不协调,这是导致中国城乡和区域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之一。
3.3加剧了城市社会发展的失衡
在传统的粗放发展模式下,由于盲目追求GDP高增长,忽视城市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和生态环境建设,导致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不协调,城市社会发展严重失衡。
一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测算,从1995~2005年,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下限由0.208 1增加到0.329 1,而上限则由0.217 8增加到0.345 6,分别上升了58.1%和58.7%(洪兴建,2010)。另据王敏、马树才(2009)的研究,1991~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每年以4.5%的速度在扩大。当前,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2008年,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之比达9.17,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之比达3.57,中等偏上户与中等偏下户之比达1.89,分别比上年扩大4.9%、4.4%和2.7%,其中最高收入户与困难户之比达11.68,高收入户与困难户之比达7.03,分别比上年扩大6.7%和6.2%(表3)。同期,困难户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则由24.4%下降到23.7%。
表3 城镇居民家庭按收入等级分组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变化(%)
|
年份 |
中等偏上户
/中等偏下户 |
高收入户
/低收入户 |
最高收入户
/最低收入户 |
困难户/
全国平均 |
最高收入户
/困难户 |
高收入户
/困难户 |
|
2003 |
1.82 |
3.31 |
8.43 |
24.8 |
10.40 |
6.25 |
|
2004 |
1.83 |
3.38 |
8.87 |
24.5 |
10.97 |
6.47 |
|
2005 |
1.88 |
3.52 |
9.18 |
23.8 |
11.53 |
6.89 |
|
2006 |
1.86 |
3.44 |
8.96 |
24.1 |
11.26 |
6.72 |
|
2007 |
1.84 |
3.42 |
8.74 |
24.4 |
10.95 |
6.62 |
|
2008 |
1.89 |
3.57 |
9.17 |
23.7 |
11.68 |
7.03 |
注:在全部调查户数中,最低收入户占10%,其中困难户占5%,低收入户占10%;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各占20%;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各占1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2009)计算。
二是城市居住分异现象逐渐加剧。一方面,为迎合少数高收入阶层的需求,一些城市在高端商务区、政务区中建造一些豪华高档搂盘,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正在形成一批高档别墅区;另一方面,老城区的改造步伐远跟不上形势的需要,城市棚户区、危旧房、城中村和边缘区改造的任务仍相当艰巨。据调查,到2008年底,全国居住在各类棚户区中的家庭共1 148万户,其中城市棚户区744万户,占64.8%。这些家庭大多属于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户。城中村和城市边缘区则往往成为大量外来流动人口的聚居地,基础设施和环境卫生条件差,社会治安较乱,“脏乱差”现象突出。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加剧,必然会造成空间隔离,诱发一系列社会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三是城市贫困问题日趋严重。近年来,中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规模明显增加,城市贫困发生率逐步提高。目前,尽管学术界对城市贫困人口规模的测算差别较大,但大部分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大约在2 000万~3 000万人之间(魏后凯、邬晓霞,2009)。这些城市贫困人口大多为下岗失业人员、长期病伤残人员、特困职工以及其他特殊困难群体。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人口达到2347.7万人,占全部城镇总人口的3.78%。然而,按照低保标准来界定城市贫困人口,显然低估了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据对6.5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2008年全国共有5.32%的城镇居民家庭年总收入不到1.5万元,按平均每户家庭人口计算,其人口数约占调查家庭人口数的4.4%。据此推算,2008年城镇居民家庭年总收入低于1.5万元的贫困人口有2 669万人[1],而低于2万元的低收入人口达6 006万人(表4)。这些城市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其生活条件相当艰苦,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更多关注。相比较而言,低收入家庭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总数的9.9%,但其全部收入和消费性支出仅分别占3.4%和4.5%,而年总收入高于10万元的高收入家庭,人口只占8.4%,但全部收入和消费性支出却分别占21.2%和18.4%。
表4 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按收入分组情况
|
指标 |
低收入家庭(<2万元) |
贫困家庭
(<1.5万元) |
较低收入家庭
(2万~3万元) |
中等收入家庭
(3万~6万元) |
较高收入家庭
(6万~10万元) |
高收入家庭
(>10万元) |
|
人口比重(%) |
9.9 |
4.4 |
16.7 |
44.4 |
20.6 |
8.4 |
|
估计人口数(万人) |
6 006 |
2 669 |
10 131 |
26 936 |
12 497 |
5 096 |
|
全部收入比重(%) |
3.4 |
1.2 |
8.8 |
37.8 |
28.8 |
21.2 |
|
消费性支出比重(%) |
4.5 |
1.8 |
10.5 |
39.1 |
27.5 |
18.4 |
注:本表数据系根据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和城镇人口总数推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09年)和《中国统计年鉴》(2009)计算。
四是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突出。农民工是当前城市发展中的一类特殊群体,长期面临着拖欠工资、劳动保护差、子女上学难、社会保障程度低等诸多问题。从工资拖欠情况看,尽管近年来有关部门加大了对农民工工资追讨和专项检查力度,但至今为止这一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工作强度大,生活条件差,工资待遇低,社会保障缺失,是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如果按照1.4亿外出农民工计算,2008年全国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农民工比例仅分别只有30%、17%和11%左右。
五是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冲突加剧。因城市向农村迅速蔓延以及城市危旧房和城中村改造,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处置不当或者制度和配套政策不完善,致使一些土地被征用的失地农民成为了“种地无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尤其是那些快速城市化地区更为突出。近年来,全国因征地而形成的失地农民大约有4 000多万人。征地补偿标准、集体资产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就业安置、养老和医疗保障等,是失地农民最为关心,也是最容易引发矛盾和冲突的问题。
3.4加剧了大城市的膨胀趋势
由于各种资源向大城市和行政中心高度集聚产生的极化效应,导致近年来一些大城市人口迅速膨胀,用地规模急剧扩张,城市空间不断蔓延,建成区“越摊越大”。如果考虑到城区暂住人口,目前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深圳、东莞、天津、武汉、郑州、南京、沈阳、哈尔滨、成都等城市城区人口规模已超过400万,其中上海、北京已超过1 000万,广州、深圳、重庆超过800万。从1999~2008年,这些城市建成区面积从3 194.24 km2急剧扩张到8 059.63 km2,增长了1.52倍,其中深圳、广州、南京和重庆分别增长了4.96倍、2.15倍、2.05倍和1.92倍。这期间,这些城市(未包括深圳)城市建设用地从3 651.58 km2扩大到9 367.36 km2,增长了1.57倍,其中南京、广州、重庆、北京分别增长了2.8倍、2.15倍、1.86倍和1.69倍(表5)。需要说明的是,东莞由于市域范围的扩大,其市区面积由237 km2扩大为2 465 km2,加上经济的飞速发展,这期间城市建成区和建设用地面积分别增长了32.1倍和33.26倍。
表5 1999~2008年中国部分大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扩张
|
|
2008年城区人口 |
城市建成区面积(km2,%) |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km2,%) |
|
数量
(万人) |
排序 |
1999 |
2006 |
2008 |
2008年
比1999年
年增长 |
2008年
比2006年
年增长 |
1999 |
2006 |
2008 |
2008年
比1999年
年增长 |
2008年
比2006年
年增长 |
|
上海 |
1 888.46 |
1 |
549.58 |
860.21 |
886.00 |
61.2 |
3.0 |
1 153.04 |
- |
2 429.08 |
110.7 |
- |
|
北京 |
1 439.10 |
2 |
488.28 |
1254.23 |
1310.94 |
168.5 |
4.5 |
488.28 |
1 254.23 |
1 310.94 |
168.5 |
4.5 |
|
广州 |
886.55 |
3 |
284.60 |
779.86 |
895.00 |
214.5 |
14.8 |
284.60 |
306.88 |
895.00 |
214.5 |
191.6 |
|
重庆 |
879.96 |
4 |
242.82 |
631.35 |
708.37 |
191.7 |
12.2 |
242.82 |
620.44 |
694.05 |
185.8 |
11.9 |
|
深圳 |
876.83 |
5 |
132.30 |
719.88 |
787.90 |
495.5 |
9.4 |
- |
- |
- |
- |
- |
|
东莞 |
727.37 |
6 |
20.60 |
608.12 |
681.86 |
3 210.0 |
12.1 |
25.80 |
780.40 |
883.81 |
3 326.0 |
13.3 |
|
天津 |
639.02 |
7 |
377.90 |
539.98 |
640.85 |
69.6 |
18.7 |
377.90 |
539.98 |
640.85 |
69.6 |
18.7 |
|
武汉 |
596.00 |
8 |
207.77 |
222.30 |
460.00 |
121.4 |
106.9 |
239.26 |
255.42 |
480.00 |
100.6 |
87.9 |
|
郑州 |
479.45 |
9 |
124.51 |
282.00 |
328.66 |
164.0 |
16.5 |
115.60 |
196.51 |
289.92 |
150.8 |
47.5 |
|
南京 |
478.16 |
10 |
194.39 |
574.94 |
592.07 |
204.6 |
3.0 |
157.09 |
544.17 |
596.98 |
280.0 |
9.7 |
|
沈阳 |
468.00 |
11 |
204.19 |
325.00 |
370.00 |
81.2 |
13.8 |
199.89 |
325.00 |
370.00 |
85.1 |
13.8 |
|
哈尔滨 |
415.59 |
12 |
165.02 |
331.21 |
340.33 |
106.2 |
2.8 |
165.02 |
331.21 |
340.33 |
106.2 |
2.8 |
|
成都 |
405.98 |
13 |
202.28 |
396.94 |
427.65 |
111.4 |
7.7 |
202.28 |
359.68 |
436.40 |
115.7 |
21.3 |
注:本表人口数包括暂住人口。东莞城区人口只有174.87万人,但城区暂住人口达到552.5万人;郑州城区暂住人口也达到202.7万人。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1999、2006、2008)和《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09)整理。
由于城区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的急剧膨胀,有的甚至“摊大饼”式外向蔓延,造成城市交通堵塞,住房拥挤,房价过高,资源短缺,生态空间减少,环境质量恶化,通勤成本增加,城市贫困加剧,公共安全危机凸现,致使一些大城市出现明显的膨胀病症状。尽管目前中国城市家用汽车每百户拥有量还不高,如北京为22.7辆(2008年),上海和广州分别为14辆和19辆(2009年),但交通堵塞已经成为各大城市面临的严重问题,尤其是首都北京交通堵塞十分严重,常常被戏称为“首堵北京”。房价和生活费用高昂,生态空间不足,环境污染突出,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也是这些城市普遍面临的问题。在北京市建成区,CO和氮氧化合物(NOx)污染常年超标1~3倍(陈宣庆、张可云,2007)。
[1] 如果家庭年总收入为1.5万元,按平均每户家庭人口2.4人计算,平均每人每月仅有520元。在目前房价和生活费用条件下,低于这一标准显然属于贫困人口的范畴。
文章来源:《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