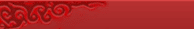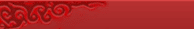|
网易财经: 您一直都非常关注中国的土地问题,然后您也多次到现场去做一些调查和调研,您认为土地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有怎么样的意义?您为什么会如此重视这个问题?
一项可协调众多社会矛盾的改革
周其仁:古典经济学讲经济怎么发展,就是几个东西放进去,投入进去,最简单讲就是那么几个东西,一个就是人力,你得把劳动力放进去,第二个就是得有资本,第三就是土地。过去讲经济就是靠三大要素,后来就增加了一个纬度,就是组织,因为你这些要素怎么有效组织起来,不同的组织办法,这个经济的产出不同,这是原来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框架。土地是财富之母,古典经济学就是这么讲的,当然会关心。
当然我的关心是和我的经历有关,因为我们下乡10年,回来以后参加了农村调查。
也有很多机缘巧合,正好发生了很多土地方面的变更,我们去看,人家也欢迎我们去看,这样就一路做过来。我的思路还是这样,就是从使用权确定以后,到了家庭,要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转让权。就是光使用权给农户,这是解决温饱的问题,因为有了使用权,他就好好的种那个地,但现在他有更广阔的经济机会,所以有时候这个地还不供他自己种,他转给别人种,转入其它用途,要把这个转让权好好发育起来。这里也要大量的用市场机制,不能完全用我们行政权去配置土地。我的看法,现在我们这个土地基本就锁在行政权这个笼子里,这个对于土地资源的很好利用,对于收入分配,对于协调很多社会矛盾是有利的。
确权是土地流转的基础
网易财经:您是把很大的笔墨都放在了土地的确权上,您觉得确权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周其仁:怎么发现的呢,就是土地要流转,可是权限不确定清的流转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这个行政权可以利用这个土地变来变去的过程中,有可能再去剥夺一道农民,把应该他享有的利益又拿走。这个危险存在,所以你在流转之前要加一个前置,这是我们在成都调查以后学到的东西,就是要把确权放进去。
确权也是受了城市的启发,我们在当地接触一位干部,他做过城市工作,也做过农村工作,发现城里人虽然城市改革晚,可是城里人有些产权界定比农村做得好,你看我们买了一个房子,它就有房产证,就有土地使用权证,都是有政府保障的你有这个权限,有了这个东西你就很容易流转,形成一个市场。可是农民世世代代的那个地,它就没有一个它权益的合法表达,没有这个表达,他要流转,就遇到很大的摩擦和障碍,所以他们就提出确权,确权是基础。我们去研究确权,发现真是很有意思,因为好多年,有些问题不理清,要从头去确权,是有难度。
城市化要处理好各种权利关系
网易财经:我看到您的书里边是提到了一句,就是未来的一个城市化可能更多处理的还是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
周其仁:它其实不光是国家和农民的关系,还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城市化不完全是一个物理的过程,就是建楼、盖房子、修基础设施,它其实里头是重要的权利关系,我们80年代的改革是把土地的使用权长久的清楚界定给农民,然后用法律来保障。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转让权,也要达到同等的水平,这样这个资源就能够按照市场准则来进行配置。当然,城市化涉及的问题非常多,它还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级不同的政府。我们现在城市化一个缺点就是这个行政性太强,就每个行政区划里头都想城市化,这个跟城市化的大趋势是不一致的,就是人往哪里流动,项目往哪里流动,它不完全看你行政级别,它要看经济机会,所以这里头还有好多经济关系、法律关系、政策要调整,要改革。
网易财经:2008年是成都首先提出了“还权赋能”,后来您也是关注成都的土地改革,您也一直在跟踪这个问题,就您看来,成都现在这个土地改革是否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周其仁:“还权赋能”是当时他们本地提出来的一个口号,就是我刚才介绍这个背景,因为比较城乡差别,除了收入、生活方式的差别,其中有一个就是权利状态的差别。为什么城里买个房子,你有比较完备的产权保障?为什么农村世世代代那么多土地、山林、房屋,你看他就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表达,到现在他也不能够抵押,所以农村金融大量的让给高利贷,它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全世界的土地都是很好的抵押资产,房屋都可以抵押,为什么我们这里就不可以?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观念上没有解决,政策上没有解决,这个对我们主观意图要发展农村,保护农民利益之间是有点拧的。“还权赋能”,第一就是农民的权利要还给农民,第二,权能,比如说它有使用权,它有转让权,它可以抵押、租赁,就这些功能要齐备。
网易财经:现在他们做得怎么样呢?
周其仁:我们观察到,它从2003年开始走这条路,就是三个集中、加快土地的整理,2008年提出了”还权赋能”,之后我们追踪了2—3年,一直到他们做确权,到2011年左右在全域范围内落下去。确权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确了权以后,这个权利流转的时候,你还要搭建这个交易平台,要让它公开、公正的进行,要把这个交易的信息让社会更多的方面了解,这样这个价格机制才更完善,所以他们也搭了产权交易所,这个我们进步我们也很肯定。我们在成都的研究做了10期,第10期以后就差不多结束了,最近的情况我也没有跟进。
土地确权工作量巨大
网易财经:据您的观察,您觉得土地确权问题的难点,最难的是难在哪儿?
周其仁:确权难的地方,因为任何一个资产的权利状况有很大的历史性,比如说一个宅基地,农村是非常复杂的,有的是土改的时候就分的,但土改是1950年、1951年搞的,离开今天已经几十年过去了,人口、社会、政策发生很多变动,我们还有一批人口是在人民公社时代出生的,他出生以后是通过集体分配给他这个宅基地。所以这中间又有符合标准、不符合标准,超标的,有各种复杂情况。
你要把它理清楚,最后就是应确尽确,就把所有边界划清楚,这是一个巨大的投入。这个投入的收益是什么?就是你有了这个投入,以后的流转就容易了。你如果没有这个投入,一流转的时候,矛盾就会拉住你,缠住你的手脚,这是我们看得到的。所以还是应该花一点力气进行确权工作。这个难度是挺大的,因为首先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所以这个工作你如果过去做了,你比如说我们过去的情况,60年的情况都清楚了,比如今年发生新的情况,我们在产权登记上做了一个修订,以后就很容易把这个财产情况搞清楚。但是你如果没有个基础,前头的陈谷子烂芝麻都没理清楚,那个难度就非常大。
网易财经:您在本书的第四部分主导机制的分杈里边有这样一段话“唯国有土地才可市场化,赋予城市土地国有制,与高度行政化的设市模式,以新的生命动力,三足鼎立,只等另一件利器,即政府的征地权出手,政府主导的中国城镇化很快就呼之欲出”。我看到这样一段话,这是否可以说土地产权问题就决定了城市化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呢?
腐败案里都有一块地
周其仁:这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基础的东西,因为它那个政府主导也不是说大家说叫政府主导它就能主导的,1988年启动了一个土地上很重要的变化,修订了宪法,在宪法里头规定,国有土地还是不能买卖、不能租赁,但是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是可以转让,这样就开了个口子。这开了个口子以后,我们才看到土地可以拍卖、可以融资,才可以看到工业和城市获得了一个新的筹资的功能,这就是土地市场化的过程。但是这个法律是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我们有更大一块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能不能转让呢?法律没有交代。而实际上就变成农民的地只有被政府征用变成国有地,才能进入到市场化转让。所以我这就是写的,叫先国有化,再市场化。现在来看,这个模式是有缺陷的。
因为你想,我这里是用政府手段拿来的地,这里是用卖的手段形成收益,你想你要是地方政府你会怎么做?他一定是这头会跟农民形成很大的竞争,希望征到更多的地,希望以更低的成本征到地。这边有盈利的东西在这里,地方要发展,财政、收入。这样就等于在制度里头陷进去一个让政府和农民利益发生冲突的体制性的挑战。
第二个后果是什么?土地相当于变成了政府的囊中之物,就是你只有到了政府这里,政府才确定哪一块是卖的,哪一块是划拨的,这样我们行政机构和官员就在土地的配置上有太大的权力。所有大的案子里头,差不多都有块地,这个地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它升值非常快,你从低价拿来,到市场价出手,这个中间差额太大了,这个利益诱惑是难以抗拒,所以这就带来几方面的不利,一方面就是跟土地有关的腐败现象越来越显现(?),第二个就是在政府手里资源分配通常分配不好,你以为低价拿来,高价销售这个体制最有效,因为低价拿来他有时候可以不那么爱惜,我们一方面说地价贵,一方面好多土地没有充分利用,闲置的土地非常多,是什么道理?这就是土地的利用机制不对头。
土地城市化高于人口城市化
网易财经:您在书中写到的特点,比如说土地的城市化是高于人口的城市化,是导致这样的原因吗?
周其仁:是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有点反常。所谓城市化就是很多人到收入较高的城市去。什么叫城市?城市就是密度比较高的空间体。结果我们所谓的土地城市化,就是建成区面积扩张的百分比比城镇人口的提高快,这不是降低了密度吗?怎么出现这个现象的?你要找到机制上的原因。
我的看法,机制上的原因,跟我们现在一手征地,一手卖地是有关系的。
网易财经:现在这个问题有一点改善吗?
周其仁:现在这个从讨论来说是已经蛮热烈的了,2008年开十七届三中全会就指出了逐步收缩征地规模,要扩大集体建设用地的市场准入。但是2008年做了那个决定以后,我认为没有认真推。没有认真推的一个原因就是2008年以后遇到金融危机冲击,需要扩大投资来带动内需,扩大投资都要用地的,所以实际上这些年征地规模是提高了,明确降低。所以实际上我们还寄希望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今年11月份的这个会议,看看能不能对此有所表述。但是从经济情况来看,从社会情况来看,这个关键领域不推进改革真是难以为继,土地资源难以为继,官民矛盾也难以为继,土地城市化的效率也难以为继。
城市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
网易财经:我看到您在您的《城乡中国》里边说,经济自由乃城市之根基,您认为目前的城市根基足够牢、足够广吗?
周其仁:远远不够。中国历史上当然很多是城市是行政化的城市,就是设一个衙门,所以我们的城过去都讲级别的,什么级别以上的衙门它可以建一个围城。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经济形成的城镇,所以城镇化的两条来路,一个是军事的需要、行政的需要,建立一些行政的管理点,然后有了官员区,有了人口的集中,然后它慢慢发展出市场,发展出经济生活,发展出民生。
你从全球看,它还有另一类城市,它实际上就是农村出来的自由民聚在一起,因为他都不继承土地。西方是长子继承权,他除了拿到传统农业社会的继承以外,他有一些孩子是自由民,然后他们就聚到一起,工业、商业、服务业是这么起来的。所以两种城市起源,在现代我们今天讲的城市化,更重要的是经济活动推进的,市场活动推进的城市化,这是经济自由的结果。
我们的历史也证明,我们高度计划体制的时候,我们城市化率是下降的。从1958年、1959年的大概百分之十九点几,降到了1978年的百分之十七点几,降了将近两个百分点,包括我们都是见证人,我们都在城里的,后来下乡了,这是倒过来的。等到经济改革,增加了农民自由以后,这个城市化率就上来了。实际上就是人往高处走的原因,就是人对哪里收入高,他会心向往之。而城市只要创造更高的收入,他就会集聚更多的人口,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可阻挡。所以我得出的命题就是经济自由。
城市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我们现在要在已有的基础上再发展城市化,需要更大的经济自由,包括金融,包括户籍,包括公民可以选择到哪里去上学,到哪里去报考,这个权利都要给公民。中国的资源是山地居多,平地很好,中国其它经济更需要相对集聚,因为集聚起来才能有足够的耕地,经济活动才能更有效。但是我们多少年来城镇化滞后,讲穿了就是经济自由滞后。所以现在要倒过来做,扩大经济自由。当然这个经济自由,各种各样的经济自由之间怎么能够更有序,这就是改革当中要研究的问题。
网易财经:您在自由这一章中开始就发了三个小结来谈迁徙自由,您认为迁徙自由是在经济自由当中更为重要的一项吗?
周其仁:当然,要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城市化。因为所谓迁徙自由就是我看到那里有一个机会,我可以过去,我可以临时去,也可以长久去,也可以搬家搬去。这就是迁徙自由,这个是1954年宪法里就写进去的,但是多少年来落实得不好。
限制迁徙自由坑苦农民
网易财经:您书里说限制迁徙自由和把农民坑得太苦是大有关系的。
周其仁:是的,因为你想一个体制如果不合理,它如果这个成员是可以跑的,你不会不合理到离谱的程度,因为你不合理他就跑了,你不准他跑,你迟早会把那个体制弄到非常荒唐的程度。过去那个不正常的饥荒是怎么发生的?很大程度上就是不能跑。所以一个体制允许能有一定程度流动,它本身也给这个体制装上一个安全阀,就是你政策不可能错得太离谱,你太离谱我就会走。可是我们多少年把这个退出权、移动权都给他封起来以后,他倒是要给我们这个制度酿成一个很大的灾难。
文章来源:投资界
|